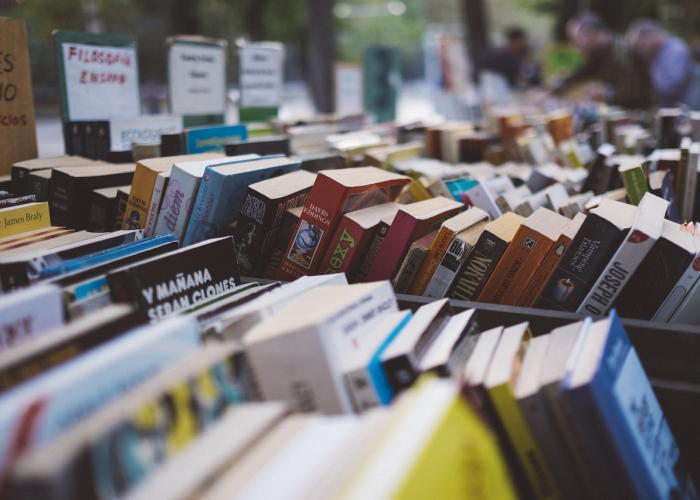“不撞南墙不死心”,这俗语像一枚生锈的钉子,楔在中国人的集体意识里,世人皆言,此语讽喻那些固执己见、不懂变通的愚者,当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,窥探其灵魂深处,一个惊心的真相豁然显现:那堵令人头破血流的“南墙”,往往并非命运的刁难,亦非现实的铜墙,而是我们亲手烧铸、日夜加固的内心堡垒。

这堵墙的砖石,名为“认知的牢笼”,我们每个人都是自身经验与观念的囚徒,坐于一口深井,却自以为拥有整片天空的视野,我们笃信眼见为实,殊不知目光所及,不过是自我预设的牢笼边界,当外界的信息如溪流般涌来,我们便不自觉地筑起堤坝——只接纳那些印证我们既有观念的涓滴,而将质疑与异见的洪流决绝地挡在墙外,商纣王握玉帛以蔽聪,终至身死国灭,岂是玉帛之过?实乃其心中早已竖起拒谏饰非的千仞之墙,这堵认知之墙,在岁月的风沙中不断加高、增厚,最终坚不可摧,让我们在自造的迷宫里兜转,将每一次碰壁,都误读为对理想的悲壮坚守。
这堵墙的灰泥,名为“情绪的沉溺”,有时,我们并非看不清墙的存在,而是不愿看清,甚至甘之如饴地倚靠其上,从那份坚硬的触感中汲取一种扭曲的“确定感”,对旧情的沉湎,对往昔荣光的追怀,或是对既定沉没成本的病态执着,都如同藤蔓,将这堵墙缠绕得更为“坚固”,也更为“温情”,我们害怕墙倒之后那片未知的空旷与选择的自由,撞墙的痛楚,竟奇异地成为一种精神慰藉,一种证明自身“曾经全力”的勋章,楚霸王项羽垓下之败,无颜见江东父老,其刚烈之气固然可敬,然何尝不是被“英雄”身份的悲情预期所筑之墙挡住了最后的生路?他撞上的,与其说是汉军的重围,不如说是自己以“尊严”为名砌起的高墙。

历史与人生的辩证法,总在绝处埋下转机。“撞南墙”的瞬间,固然是破碎与痛苦的顶峰,却也可能是觉醒与重建的起点,那一声沉闷的撞击,是旧有世界图景崩塌的巨响,头破血流的狼狈,迫使我们从自恋的迷梦中惊醒,开始审视那堵墙的真实质地——原来它并非天生地长,而是可以拆解、可以逾越的,王阳明于龙场困厄中,格物穷理,遍撞朱子学说之“南墙”,终在痛苦的求索后悟得“心外无物”,破茧而出,真正的智慧,并非来自对南墙的回避,而是来自撞击之后,那片刻清醒中的深刻内省。
“不撞南墙不死心”,其警示意义,不应止于对“固执”的浅层讥讽,更应是对自我灵魂的犀利拷问,我们是否正活在一堵自造的高墙之内?我们引以为傲的“坚持”,究竟是远见与韧性,还是恐惧与偏执的遮羞布?
真正的勇者,并非永不撞墙的幸运儿,而是敢于在剧痛中审视伤口来源,并积蓄力量,推倒那堵墙的人,当他穿越废墟,踏上未知的旷野,他会发现,曾经的铜墙铁壁,不过是一道虚影,一道由怯懦与偏见投射的幻象。
推倒内心的高墙,世界方才真正无垠。

 微信扫一扫打赏
微信扫一扫打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