火车轮毂与铁轨的撞击声规律地敲打着夜晚,窗外流转的灯火如散落人间的星子,我靠在略显斑驳的车窗上,闻着行李架上邻居带回的月饼若有似无的香气,突然意识到——这已是我离乡后第十七个中秋归途。
壹
记忆里的中秋,总是从母亲晾晒的桂花开始,老家庭院那棵百年桂树,每到农历八月便缀满碎金,母亲会选晨露未干时采摘,她说这样的桂花香气最醇,后来我去了北方城市,才发现超市真空包装的桂花糖,永远复刻不出母亲指尖的温度。
今年返乡的行李里,装着公司发的豪华月饼礼盒,金丝楠木包装,雕龙画凤,内衬丝绸,八枚月饼宛如艺术品,但我知道,在母亲眼中,这远不如我大学时用第一份兼职收入买的简装五仁月饼。
贰
列车停靠小城时,月正圆,站台上挤满了接站的人,他们踮脚张望的眼神,让我想起迁徙的候鸟,父亲的身影在人群里格外显眼——他固执地举着写有我名字的纸牌,尽管我每周都和他视频,接过行李时,我触到他掌心厚重的老茧,那是岁月写给游子的无言诗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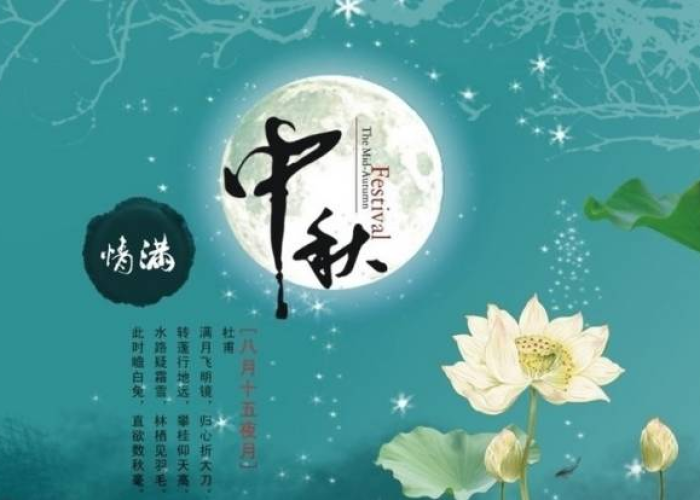
老家巷口的石榴树又结果了,红艳艳地垂在青砖墙头,邻居阿婆还坐在树下剥豆子,见了我眯眼端详好久,才用方言唤出我的乳名,这种被土地记住的感觉,让在都市编号生活的我瞬间破防。
叁
家里的团圆饭永远充满仪式感,母亲坚持要用古法制作芝麻糖饼,她说机器压的月饼没有灵魂,父亲在院子里支起旧石磨,我推磨他添米,就像童年时那样,糯米浆流淌的乳白色,在月光下泛起珍珠般的光泽。
饭桌上摆着“三样必备”:祖母传下的青花瓷盘盛着苏式月饼,父亲手雕的南瓜灯里点着红烛,还有那套缺了口的酒具——据说是曾祖父逃难时唯一带出的家当,这些带着家族记忆的器物,比任何奢侈品都让我心动。
肆
深夜与父亲对坐品茶,他忽然说起家族往事,太爷爷那代中秋夜要祭拜天地,爷爷那代要在月下读家训,到了父亲这代,仪式简化为吃个月饼。“到你这里,”父亲顿了顿,“连月饼都要赶着假期最后一天才能吃上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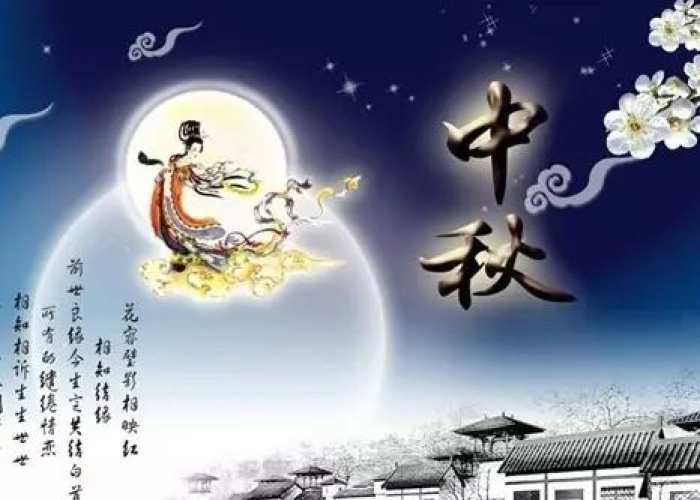
这句话让我怔忡良久,我们在城市追逐的所谓成功,是否正以割断文化根系为代价?表哥在家族群发来VR中秋祝福,科技感十足却冰冷如月球表面,而小侄女对着手机喊“嫦娥阿姨”时,她是否知道月亮上其实没有玉兔?
伍
启程那日清晨,母亲在天未亮时就起床炒制桂花糖,她说城里买的添加剂太多,坚持要给我装满满三罐,父亲默默往我行李箱塞了本黄历,在“八月十五”那页折了角,上面有他娟秀的小楷:“月圆人圆处,便是心安时。”
高铁启动时,我打开母亲准备的便当——月饼被细心切成小块,旁边放着剥好的石榴,突然明白,中秋返乡从来不是单纯的空间移动,而是精神世界的溯游而上,那些被我们笑称“老土”的习俗,实则是文化血脉的毛细血管。
终
如今我的手机相册里,珍藏着这次返乡拍的43张照片:有母亲凝神制作月饼时鬓边的白发,有父亲擦拭祖传月饼模子时专注的侧影,还有院子里那盘用古法制作的月光饼——饼身特意留了处焦斑,因为祖母说过,完美的月亮反而失了真趣。
月亮亘古不变地圆了又缺,而中秋返乡的路,是我们这代人在时代洪流中为自己保留的文化锚点,当都市的月饼越来越像奢侈品,故乡灶台那炉带着烟火气的传统月饼,依然固执地守护着关于团圆最本真的定义。
(全文共计1376字)

 微信扫一扫打赏
微信扫一扫打赏

